中国农村网 > 文化园
化解花木兰式文化困境
2016-01-14 16:35:16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午荷
对话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兴:《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

作为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专家,电影与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一直有着超高的人气。她还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先驱和推动者,因而有“中国的苏珊·桑塔格”之美誉。其智慧与锋芒已成学界“传奇”。
那么,在她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花木兰这个经典符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隐喻?作为女性,怎样实现个体突围、获得真正的幸福?……在不久前记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次以女人书写女人为主题的读书活动中,我们有幸请到了戴锦华教授与读者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于是,受本报委托,《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与戴锦华老师进行了一场“他问她答”的精彩对话。
物质和精神的女性生命困窘
高兴:在美国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短篇小说《花园小屋》中,女主人公出身于一个有着音乐追求的家庭,但是从小饱受物质的困苦,于是她觉得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物质的问题,就在20多岁时嫁给了华尔街一位金融巨头。但是,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内心的一些东西又开始萌动了。一个她崇拜的歌唱家又在瞬间唤醒了她内心的幻想。只是主人公在一番梦醒之后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最后这个有着精神象征含义的花园小屋还是要被拆掉的。这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结尾。
威拉·凯瑟这个小说实际上涉及物质和精神内在的一些关系。戴老师,您长期研究女性心理,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专家,对于威拉·凯瑟这样的女作家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有何高见?尤其是在目前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下,女性如何在物质和精神这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戴锦华:我说一点自己的体会。应该是1987年,我第一次自称Feminist,当时好像还没人如此自认,我刻意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有人认为我是为了回避男权,不错,我也自嘲过自己是“没牙的女性主义者”。但这样翻译,是因为我认为女性议题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议题,而不是权利的议题。但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激变,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考虑把Feminist再次译为“女权主义”,因为妇女的权利已经重成社会议题。
当年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女性主义还是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与我们的现实差异甚多,而今天我们已进入到全球同步的生存状态当中,几乎没有根本的差异性,现代女性也似乎处在一个解放、自由和充满选择的生命状态中,同时我们也深深地落到了一个女性主义得以产生的生存现实、生存结构和环境中,以至于威拉·凯瑟在100多年前撰写的《花园小屋》中提出的关于物质与精神、关于女人是嫁得好还是干得好的问题,女性物质的生命保障、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满足、精神的慰藉是否是一对矛盾的问题,突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
高兴:豆瓣上有篇书评说,小说是世界留给女人的“钥匙孔”。从这个“钥匙孔”看别的女人的故事,往往能从中发现我们自己。作品中一些桥段就像真实地发生在今天。
戴锦华:今天,多种的选择成为可能,而种种的选择也是以种种的平等或不平等为前提和代价的。坦率地说,我不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也不可能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先要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否则“娜拉走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尽管我对最后这句始终有所保留。可同时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谈到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时候,人人都会提及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但她对这一独立空间的重要的条件却很少有人提及:自己的支票簿。换句话说,独立的生命空间是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物质的保障联系着经济独立,你可以去换取,但他人的赐予、换取,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不付钱的午餐”。我经常说,我不反对任何女性做任何一种生命的选择,但当事人得清楚,经济的独立、理想的实现和精神的满足,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同样,就是嫁得好,过富足的生活,被人供养,可以买很多包,一样也要付出代价。那么哪个更无法承受?只有你自己知道。
高兴:可见威拉·凯瑟等女作家自19世纪以降的探讨是极具现代性的。
戴锦华:她们的作品非常细腻地、非常平常心地、非常有文学性地展示了女性生命当中的困窘——有些时候是人的困窘,有些时候是只有女性才会遭遇的困窘。
男性被锁死在父权结构中
高兴:您曾说过,“女性主义让我懂得社会规范是压制着女人和男人的,男人在这种规范中受益,也受伤害”。您还说,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对任何人来说,婚姻都是冒险,但是值得一试。”因为婚姻是幸福感来源非常重要的一种。您的这席话让我认识到女性主义者并不是张牙舞爪的、与男人为敌的,而是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您能具体描述一下这种完美的两性关系的愿景吗?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智慧?
戴锦华:(笑)这是鹊桥心理诊所、“幸福到永远”咨询公司才能回答的问题啊。我们总说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尽管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数码时代、“宅”时代,2013年好莱坞拍摄的《她》(Her)向我们展示某种未来:独自而不孤独。片中孤独的男主人公可以与自己的电脑操作系统——化身为一个女性的声音共坠爱河,很温暖,也很恐怖,似乎在未来,人不再需要人。走出电影院时我想到了一个煞风景的问题:假如停电了怎么办?
迄今为止,人仍是社会性的存在,人需要人。尽管这几十年来,我们持续经历着社会的碎片化,家庭也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于是,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对吧?人需要人,人需要和人在一起。但是任何两个独立的个体的结合都是艰难的,不仅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问题的特殊,是在于他们同时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父权结构当中,而男人整体被父权结构命名为主人,或者说是统治者。作为女性,恐怕首先要明白,就是男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居统治地位、优势地位,但同时男性也被锁死在父权结构当中。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一个女性的所谓失败者和一个男性失败者的遭遇恐怕非常不同,因为父权逻辑设定男性必须成功、必须在主流结构中占位置。而女性的失败尽管同样伤痛,却被社会目为“正常”,因为原本就没想让你入围、入局和加入竞赛。这是主流逻辑的悖谬。
所以,作为一个女性,你首先要明白,一方面男性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男权逻辑的囚徒。其次你要认识到,男权逻辑借重男性神话,如果你相信类似神话,大概只能为自己的受害负责。比如男性生而高大阳刚、孔武有力、聪明能干,必须获得成功,必须封妻荫子,必须让你买得起很多包。
高兴:而且是LV的。
戴锦华:如果你相信这个东西,你一直在寻找能够给你提供这一切的男性的话,恐怕很难说你会获得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是不是会对你身边的每一个男性、你生活中的男性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
高兴:我作为一名男性,很感谢戴老师这番话。
戴锦华:还有,作为一个女性,你是否意识到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并不小于男性和女性间的差异?我一直说有柔情似水的女性,也有阳刚勇武的女性,就像《刺客聂隐娘》的主人公,侯孝贤导演说男刚强、女性烈,如同可能有强悍的女性,也注定有极柔弱、纤细的男性一样。如果你能理解个体差异,也许就能窥破神话;也许你选择你的伴侣、获得幸福的机会会大一些。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我才会谈对男性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说女性整体同情和理解男性。没那么自作多情啊,我们更紧迫的是争取更多的女性空间,让我们能够发声,能够表达我们的生命经验。
至于如何才能幸福地生活,我已经说过任何两个生命的结合都是艰难的,都需要更多的聪颖和智慧。要想让爱长存,仅仅凭爱是远远不够的。这里说的智慧包括相互理解,包括坚持和妥协。爱使人盲目,但是盲目地爱着未必幸福。不好意思,这话说得已经挺像心理咨询医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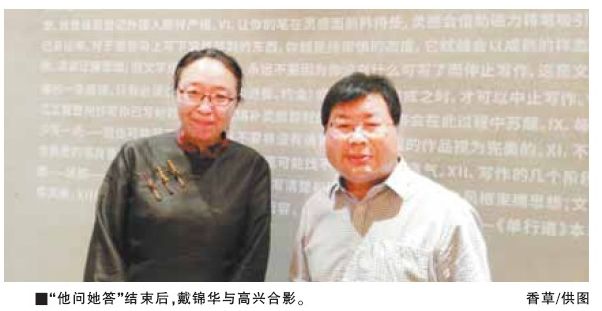
以性别为表述的写作意义
高兴:前面的话题实际上都是超越文学的,让我们稍稍回到文学本身。现在有一些作家对所谓的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像捷克现已定居巴黎、已经把自己塑造成法国作家的米兰·昆德拉,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实际上都充满了不忠,时时刻刻想着背叛,也就是说,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负面的印象。而捷克另一位作家伊凡·克里玛笔下的女性人物,却特别温柔、美好,充满了理解心和对话的可能性。这两个作家我都接触过,问昆德拉怎么看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他说文学不应该存在性别,我们只是具体地看每一部作品。而克里玛恰恰相反,他说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之所以那么美好,是因为他热爱女性。有一次在他家里,趁着他夫人到洗手间的刹那,他凑过来以男人的方式对我悄悄地说:“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是我拥有过好几个优秀的女性。”他还说,和女人你什么都可以谈,和男人除了喝喝啤酒,除了谈谈足球,你还能聊什么?可见不同的男性作家对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姿态。我想问问戴老师,是否认为有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这种性别特色的文学存在呢?
戴锦华:对这个问题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认为所有加前缀称谓的都带有某种歧视性: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这意味着他们是某种弱势群体。似乎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更宽容的标准,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衡量他们。事实上,就女作家而言,古往今来,有太多的女人是她们自己时代最优秀的作家,无需前缀。我自己也一向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双重标准。这算是我的文学艺术立场吧。但换一个角度,我也始终赞成女性文学的命名。感谢你举了米兰·昆德拉的例子,他也是我喜爱的作家——因为他的睿智和幽默。但是我一向不喜欢昆德拉塑造的女性角色。
我不喜欢的原因不在于你所说的“不忠”,而是一种高明的定型化。事实上,我自己认为昆德拉笔下有两种女性形象,一种是所谓的“不忠”——自由、狂放与男人一般地“猎艳”。而另一种是“永恒的母亲”——忠诚的女性。而昆德拉笔下的男主角,我称之为“忠实的登徒子”,这类男人通常处处艳遇,但是他心中的爱只属于一个女人——那个忠贞的母性的女人;在他的艳遇中,他是猎人,也是猎物。
这也正是我认为需要女性文学的原因。为什么说她们笔下的她们和他们笔下的她们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在于,只有在女性笔下我们才会遇到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繁复而真实的女性。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男作家——即使是才华横溢的旷世奇才的笔下,能读到的女性类型也极为有限。有位日本的文学理论家做了一个最宽泛的分类,认为古往今来文学历史上有十五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电影理论概括得比较简单,仅五种而已:大地母亲、贞女、荡妇、女巫(不可思议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女童也可以说是祭品。男性所写的女性很容易归到这几种原型当中去。
但是,当我们读女作家的作品时,即便是那些按照某种规范去书写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仍然看到很多溢出,看到很多在男作家笔下那些类型化女性身上找不到的表述和时刻。因此,女性的书写,女性关于女性的书写与男性的同类书写大有不同。
高兴:确实如此。
戴锦华:这同样又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当中,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权的文化,我们只能在其上叠上我们自己的书写。我们看汉字已然很清楚,看欧洲语言,比如英文就更清楚:man,人就是男人,历史是history,哪有“herstory”。女性在男权文化中是内在的、当然的他者,作为the other,女性文化的意义是什么?补白或颠覆男权文化。因为男作家笔下每一种女性类型都负载着某种男性生命困境:或成了其生命灾难的成因,或成了其救赎想象。所以我几乎从不用正面、反面的女性形象来讨论类似问题,正面或负面,只是相对于男性的心理、文化功能而已。我一直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尤金·奥尼尔的面具戏剧《大神布朗》。剧中唯一一个具有救赎力的形象——男主人公最后死在她的怀抱里——是这样的,她戴上面具是荡妇——一个妓女,摘下面具则是大地母亲——几乎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一个性感的但又拥有无限包容的母亲,她在魅惑你、满足你,并在任何时候接纳你的一切。
女性自然也有对男性的梦想。女性的通俗写作也经常塑造种种白日梦式的男性角色,如父如兄。当然,等而下之的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又译《五十度灰》)了——所谓霸道总裁爱上我,没理由,不解释(笑)。但是更多的时候,在严肃的女性写作中,男性的视点同样丰富或丰满了男性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我们还没能彻底改变性别的权利结构的时候,恐怕以性别为前缀的写作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女性主义的意义不在男女平权
高兴:总体上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刚才戴老师已经说过了,这天还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权的文化。那么,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您觉得女性如何才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她们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某种自由和平等?
戴锦华:一方面,历史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比起100年前,吴尔夫在写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她还没有资格踏进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中国女人还在缠足,只有妓女可以出入于社会空间,今天我们能自主选择或是努力的空间已不知拓展了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对于现实、对性别权利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有足够了解的话,当然可以做出对你自己说来正确的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充分的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当性别依然是桎梏,尤其是它在一个高度资本化的过程当中被不断强化,而且落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置身于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个体所能做出的选择又是极为有限的。很多事情不是光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就能达到的。今天我们所能把握的,是对现实有清醒的理解、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追求独立、实现理想必然要付出代价,追求某种隶属、某种附庸、某种出售、某种交换当然也有代价。那么,你想好了吗?你能够承担吗?如果你有把握,那么这是你的选择,也许能成就你的幸福。
高兴:有选择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而在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离别的礼物》中,女主人公从很小开始就不得不饱受着家庭中一种痛苦的迫害,也就是成为她父亲的性发泄对象。这是一篇特别压抑而且极为残酷的小说,让人惊异于人性的黑暗,同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父权制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戴锦华:这篇小说我几乎不想读下去,因为它传达了一份普通而极端的苦和痛,在我的体认中,它是如此真切。它一而再再而三令我想到——既想到奥菲莉亚的宿命,也想到打工妹,无数的打工妹的命运。其实相对于生活在贫困、艰难、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的女性,我们真的太奢侈了,可以坐在这儿谈我们的选择,有多少女性完全没有选择。比如那些“嫁给大山的女人”。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文化悖论,即女性主义本身是一种现代主义,说白了很简单,女性要求分享男性在现代社会当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女性经常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拥护者和积极的投入者。但是矛盾和悖论在于,当现代主义自身的问题凸显时,人们会回首、反思、怀旧于乡村、故乡。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现代性反思的,但在每一个认同时刻,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如何面对前现代结构中的父权压迫,那些最丑恶、最直接的践踏、蹂躏、剥夺?
高兴:所以说,这篇小说特别能反映出当代一些普遍的问题,尤其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问题。
戴锦华: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男女平权,更不是两性对抗,而在于以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作为新的文化资源为世界提供想象力空间和新的创造。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现代逻辑,不同于男性逻辑、父权逻辑、资本逻辑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不是回归父权主导的昨日、故乡,而是去想象和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别样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当中,我们有平等、有自由、有选择,但这一切不是过度的开发,不是对发展主义的盲目信任,不是对资源无穷的榨取。因为女性的生命是生产性的,所以女性的生命经验当中包含的并非消耗性的、占有的、征服的东西,也许我们整体的生命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去打开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最富意义的部分。
高兴:这样的话,整个世界才能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我还想说更加合理,这是特别具有建设意义的。
解放的代价:花木兰式处境
高兴:在您阅读的大量优秀女性文学作品中,有哪部作品在深刻性、复杂性——我指的是处理两性关系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锦华:我刚好想到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神圣祭坛》,她在作品中描绘了两性关系的极端微妙之处:如果一个女人成为男人精神上的知音,如果他们真正达到了精神上的平等,在他那里她就不再是女人。这种精神上的深刻理解和平等的交流,就似乎取代了、也取消了一切性别之爱的可能性。这同样是重要的,是解放了的女性所面临的另一种困境。
高兴:男人面对智商较高的女性,多少有点心虚吧,不敢拿她当女人。
戴锦华:前一段时间我又重提了类似话题,即广义的花木兰式处境:一个自由解放的女性,进入社会生活的前提,是“化妆”为男性,因为社会生活的全部规范都是男性规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领域当中,评价标准当然同样是男性标准。介入社会生活就意味着你必须以付出、掩饰自己的某些性别特征和需求为代价。而女性的另一个“古老的”困境,是被迫藏起自己的智慧,“化妆”成“女人”。
我很好奇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位捷克作家,他说他“拥有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是什么意思?拥有她们的肉体或心灵?他与她们倾心相爱时,是否也倾心畅谈?我们都知道那个古老的偏见:女人是没头脑、非理性的,女人与哲学无关。而可笑的是,这样的女性通常是被男人热爱的女性。还是我熟悉的例子——玛丽莲·梦露,今天大家已知道她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女人,但在银幕上,她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女郎。大家更熟悉的就是麦当娜,她在中学时已开始自修大学预科的课程,成绩优异,经常辅导男同学。但她发现自己却是唯一一个没人追求的女性,这以后她开始扮女性:性感,同时无知(笑)。
高兴:那么,女性怎么化解花木兰式的文化困境?在一个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当中,如何做出自己的个体选择?戴老师能否给女性读者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和可行性建议?
戴锦华: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在当今女性权利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女性对自己、对现实、对性别权利有清醒的认识,还是可以做出智慧的选择,并获得自己的空间,参与到历史创造、改变现实的过程中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鼓励大家的,但是我真心推荐大家博览群书。读小说的快乐和收益将伴随你一生。我自己从童年时代开始,为了面对孤独,也是为了面对成长的烦恼开始大量阅读——我说了太多次了,我11岁时已经一米七了,一个女孩在那个年龄就长到这么高,高过所有的老师,而不只是所有的同学,那种痛苦,背后的戳点……阅读一直是我的庇护所,是我的洞穴、我的家。我有把握跟大家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陪伴你一生的宝藏,你阅读了,记忆了,你将拥有谁也夺不去的宝藏。有一天你真的一无所有,漂流荒岛,遭到囚禁,你仍可以在心里打开这些书。我相信这个说法,读50本有选择、有质量的书(可以是小说,可以是电影),足以改变你的人生。这是我的体会,不是我的训诫。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