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网 > 往事
鼎革时期的奉化小乡绅怎样经营孤儿院
2016-04-19 20:38:57 作者:澎湃新闻成梦溪
张泰荣(1902-1978),浙江奉化人,参与发起成立奉化孤儿院并历任募捐主任和副院长,是民国时期奉化慈善事业的中坚人物。他1922年至1957年的日记近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奉化解放前后的日记,颇可见历史转折时期对普通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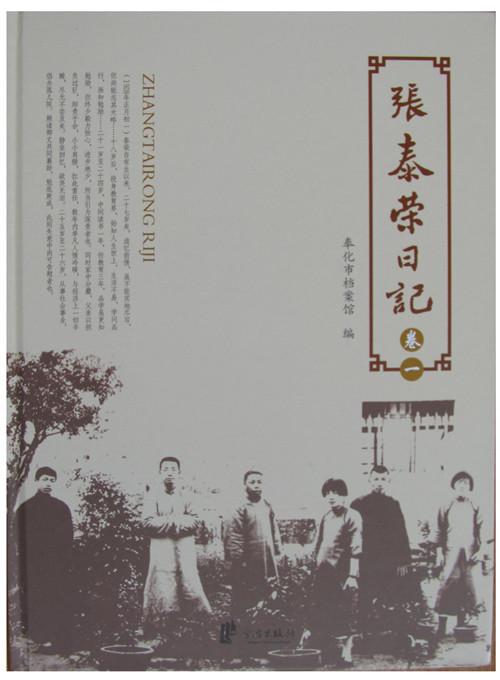
《张泰荣日记》
1949年5月25日,对张泰荣来说仍是平静的一天,他一如往昔地处理奉化孤儿院的闲杂事务。孤儿院所养之蚕依旧默默做茧缫丝,家里水田需要下种,被日军损坏的房屋的原地已砌起新房,接近装修尾声,一切都安然无恙。
然而,就整个奉化县城而言,这却是不平静的一天。这一天,奉化城内悄然呈现了权力真空状态,国民政府和军队陆续撤离,中共军队尚未到来。政权的更迭,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各种变数都存在着可能性,最是令人惶恐不安。
这一场景并不让人感到陌生。时光转回四年前,日寇带来的无边黑暗于1945年结束,重建家园成为当务之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1945年日本投降、孤儿院回迁返城,张泰荣对未来充满着向往:“余当埋首苦干,复兴建设,余之事业自有更愉快甚于今日者殆无疑义,余其勉之。”(1946年1月1日)尽管做公益事业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但他始终具有自知之明,并未试图谋取要职,即使有机会也借故推脱,只愿认真做事。他对自身的定位一直十分清晰:“国事、县事余无过问能力,亦无责任可言。地方建设,如八乡会馆、奉中镇中心小学,余必竭尽绵力促其成功。”(1947年1月1日)对张泰荣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与其卷入政治中浮沉不定,不如全身心投入地方公共事业中去,苦干以见直观成果。
1948年至1949年,是时局陡变的一个阶段。有些现在看来清晰无比的事件,在发生的当下,却是混沌。尽管这一年物价忽涨忽落,人心也随之忽上忽下,但普通人对时局变化的感知总是滞后的。彼时,东北战场上国军一败涂地,辽沈战役开打在即,国民党败象已显。而奉化城内各政治人士,仍于四五月间商讨派代表赴南京向年初当选大总统的蒋介石道贺。
然在北京和上海,距离政治中心更近的人们已经感知到了浓郁的紧张气氛。胡适于1948年10月便体会到了急转的形势,在日记里写下:“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他甚至一度想要投身政治,“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当然,此刻立下政治志向为时已晚。居于上海的颜惠庆同样发现人群中弥漫了悲观气氛,且上海于11月11日开始实行宵禁,紧张氛围更甚,他的部分友人开始迁往台湾或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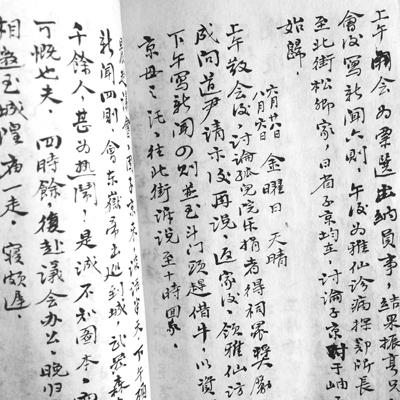
部分日记
到1949年初,张泰荣等普通民众已然觉知时局似要走向另一边:“默察今后时局,周视环境迥异既往,即本院经常支持已感非易,房屋建设应视情形,其他事业恐更无余力。”(1949年1月1日)随着日子一天天推移,政权更迭的迹象也逐渐凸显。
纵然时局移易,但更多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心怀希望,继续往常生活。颜惠庆尽管曾接受李宗仁的委托,作为“和平代表团”之一奔赴北平商谈。但到抉择时刻,他并未应李宗仁的提议迁至台湾,而是留在上海,顺利等到5月25日共产党正式接管上海。其时,甬籍商人秦润卿亦留居上海,以他所见,解放之日沪地“秩序良好,各业纷纷开市,照常营业”。
将视线转回奉化,5月24日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陆续全部撤出,权力真空状态不过持续一天,5月25日下午五时共产党军队开到接收,奉化即告解放。解放军进入奉化县城内的第一天,纪律严明,整齐有序,且张贴八项文告以定民心,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张泰荣等人怀揣着一份欣喜与新鲜的心情迎接新政权的来临,“人民聚观,途为之塞”(1949年5月25日)。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突然更迭似并未引起民众的过多思量,生活与工作一如往常。
晨光渐露,新政甫定,一个融合和适应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新政权的风格亦与旧制完全不同。在此环境中,张泰荣所主持的奉化孤儿院在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套运作模式逐渐出现缺口,困境频现。
首先,资金和粮食来源出现问题。孤儿院在募捐和银行存款之外,基本依靠田地,以获得租金及租谷。孤儿院经营近二十年,不动产数量颇大,“计慈溪田106.996,本县出租田733.5855、山十亩、屋平三间半、楼二间,自种田73.406亩、山227亩、地12亩,租入田22亩5分、地1亩3分”(1950年11月7日)。随着新政的出现,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直至田地大部分被收回,孤儿院原有的租金、租谷无从收取,必须另辟蹊径。
其次,对外募捐部分产生障碍。原先主要是奉化籍旅沪商人的资金支持,1949年后部分商人离开上海出国或出境营生,部分商人经营失败破产,钱庄亦大多倒闭,使得孤儿院资金来源缺失大半。幸而张泰荣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甬籍商人胡嘉烈,其公司主体在新加坡,并未受到当下战争的波及,因而尚有足够资金继续支持孤儿院。
再次,新政权肇始未定,政策不明,上下沟通不顺,使得运作不畅。如政府某日开会时通知人们可将孤儿认领回家,但大多数孤儿尚有亲属,无须被陌生人领养,引来解释困扰。又如政府拟借用孤儿院房屋,但未传达清楚究竟是借全部还是部分、是借用还是使用,使得张泰荣不免犹疑孤儿院的存续问题,“不知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阶段,是否需要此种事业存在,值得考虑耳”(1951年8月15日)。
种种问题,是新旧交替之际所必然会面对的,在一开始的新鲜和欢迎之后,此时的纠结、彷徨无措及焦虑之感,是人需体会的必经之路。这并未击垮张泰荣,而是让他更用心地重新发掘孤儿院的经营方式,以与新政权更好地融合。
既有运营方式出现问题,幸好工业方面尚能努力。建国之初,政府对工业十分重视,亦支持孤儿院人士自主办厂。张泰荣自1951年起便奔走于杭甬沪之间,获得政府办厂许可、筹集办厂资金,最终创办起麻袋工场与精洗工场。土改开始之际,孤儿均可回乡领取分配的土地,大部分孤儿因此归家,孤儿院规模大为缩减。同时,张泰荣亦因时制宜,调整布局,将教育部分移至山区项岙、城内办理麻袋工厂、重新安排教职人员及分配年级。孤儿院不再如昨之冗大,孤儿仍有出路。

奉化县孤儿院第五届毕业留影
政权及政体在历史书写中总是叙述的焦点,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政界要人李宗仁、学界翘楚胡适、职业官僚颜惠庆、工商巨子秦润卿,他们对江山换新颜的感知各有不同,相比乡野村夫,对家国天下的走势自有一番或欣然或忧郁的情怀。就普通人而言,当下的“改正朔、易服色”或许未必那么有冲击力,但或明或暗的改造却如“润物细无声”般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以张泰荣的经历可窥知这一影响至深至远、自上而下地散落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人都能感受并体验之。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严格的归属感,新旧政权交替之中,张泰荣固然曾感叹过去,但迅即调整状态迎接未来。
适应大环境的更迭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张泰荣经历了自欣喜到彷徨,再到振作适应的过程;但也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因为他始终抱持积极的心态去融入新政权。日记中的语言风格变了,阅读世界也大不相同,这些都映射出了张泰荣力图融入新社会的努力。
工作方式亦如是,老一套办法走不通了,及时调整,重新选择侧重点。未来这条路,不停变换着方向,谁能预见每一次的历史转折?与其毫无把握地试图预见未来,不如像张泰荣那样脚踏实地做力所能及之事。
无论周遭如何变幻,埋首干实事,是值得记取与弘扬的人生态度、人生准则与价值观。尽管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不免微渺,但作为一种精神,则具有无尚力量。
昨日的世界在昨夜死去,晨光熹微中埋首做去,总能触及鲜活的种子。(文/成梦溪)
责任编辑:王萍